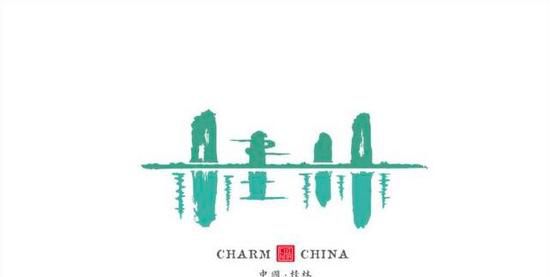06年经典译文之美国文学:美国幽默和西部的兴起(二)
|
美国绅土派文人,在写作和做人方面,拿给欧洲人看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美国。欧洲人在他们那一方面也有反应。按照惠特曼在《诗人与其计划》('The Poet and his Program', 1881)中引自伦敦《泰晤士报》的话,说著名的美国诗人"已经完全掌握到了英国的情调、态度与心情,那些阅历不深的英国知识份子简直要把他们看作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了"。他们的作品读起来颇为有趣,"可是从头到尾都严重地缺少一种新鲜的风味"。比如说洛威尔,"当政治激起他的诗兴时,他的作品洋溢著美国人的幽默;但是在纯诗的领域里,他的美国气质还不如一个地道的英国人"。《泰晤士报》在这里讨论的是美国需要一种本土文学,其热情并不下於美国人自己,不过也同样缺乏始终一致的观点。他们认为朗费罗和洛威尔是新英格兰人(所以是美国人)而非英国人,而且他们写起歹徒来本事也并不比斯蒂芬和阿诺德大(偶有例外,比如《比格罗诗稿》)。当一个真正的美国歹徒出现时,英国人会对他愉快地表示欢迎,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而在美国人心目中却是存心侮辱),相形之下,洛威尔和朗费罗倒有点像是假货了。一八七O年继莫特利之後出任驻英公使的是一位申克将军。莫特利是个学者,绅士风度,公使做得不错。可是申克将军由於把换牌扑克游戏带到伦敦,使他成了社交场上的红人。玩这种游戏需要胆量,他多年的实践使他有的是胆量,所以玩得很好。不幸的是,他同一个可疑的采矿生意有牵连,使几个英国朋友著实破了钱财。他罢官回国,又一次证明了英国人一贯的看法∶美国人有点怪,也很有趣,但是都没有教养。 可是英国人比大多数美国人还要著急,很想能够早日看到真正的美国本土文学的苗头,有时,那怕只能满足他们对於美国生活的想像也行。惠特曼的作品,由於罗塞蒂的推荐,在英国所受的欢迎比在美国还要普遍。在美国内战期间和战後,英国人对於真正美国文学的向往,总算得到了满足。阿蒂默斯·沃德的讲演和他在《笨拙》杂?上发表的文章;"俄勒岗的拜伦"乔奎因(又名辛辛纳特斯)·米勒的人品;布勒特·哈特描写西部矿区生活的诗歌与短篇小说;乔希·比林斯的箴言和马克·吐温的作品这些篇章以崭新的活力闯入伦敦文坛,其气势有如近年的美国音乐喜剧。和《俄克拉荷马》与《飞燕金枪》一样,它们并不能适合所有读者的胃口。苏格兰批评家约翰·尼科尔在他的《美国文学》(1885)一书中,反对某种美国幽默的"堕落风格",他特别指出,马克·吐温"败坏了英语国家的文风,甚於任何一个当代作家。"不过大体说来,英国批评家对於新兴的"西部"幽默,态度要比美国本国东部人士和缓得多。豪威尔斯这样解释∶西部在文学上初露头角时,可以完全不管比较古老比较文雅的外部世界,但我们东部却总是怀著恐惧的心情瞧著欧洲,一方面急於要出人头地,一方面要描写自己。 "西部"或"边疆"幽默,其实不只限於西部。它的某些特色,在新英格兰和"南方东部"幽默中也可以找到∶比如说夸张的习惯(洛威尔描写一间木板屋"漆得真像云石,一下就沈到水里去了"),是由东部人首先养成然後才传到西部去的。沃德和几个别的幽默作家都来自东部。哈特是在布鲁克林和纽约长大的,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对於他所描写的矿场生活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乔奎因·米勒,正如《泰晤士报》评论中所说的,一点都不粗鄙,虽然他在衣著和态度上给人以粗鄙的印象,"他的诗句谐和流畅,可是谈到思想,他那些歌颂高山的诗,就是在荷兰也可以写得出来"。东部和西部在意念上的不同,就像他们区域地位的不同;在这方面东部有一点反对西部作风。海约翰出生於西部的印第安那(许多西部人来自那里),老年时期那个温柔娴雅的海约翰,实在不像青年时代那个以《派克郡的民谣》(Pike County Ballads, 1871)受到美英读者宠爱的海约翰。纽约作家斯特德曼在一八七三年对一个朋友说"整个国家┅┅已经淹没、泛滥、沈浸在俚语、庸俗┅┅鄙野和并非机智的插科打浑的浊流里了,"几个批评家对於海约翰的《派克郡民谣》的幽默,也不比斯特德曼客气。三年之後,一个东部的写书评的人把印第安那一位作家写的一本书说成"从山那边侵入的哥特人"的作品。 这句话透露了不少消息,虽然那位书评家大概并没有影射他所代表的假罗马文明已经注定要毁灭。为了要了解哥特人的头子马克·吐温,值得我们去把这个哥特人盘踞的地方检查一下。美国的哥特人区域包括了几个完全不同的地区∶ 旧日的西南部、边境矿区、和太平洋沿岸,只举马克·吐温熟悉的这三个地区就够了。但是我们可以概括地把这些地区整个称做西部或边疆,来形容某些仍在定居过程中的美国地方。其中大部分是荒野,在初期移民到达以前,这些地方只有印第安人、白种猎人和设陷捕兽人散居。生活非常艰苦;他们所以能够活下去,完全靠的是自力更生,这样一来,他们就养成了一种藐视法律、文雅的谈吐和社会习俗的态度。在一八四二年游历美国的狄更斯,在一条驶往匹兹堡的运河船上首次碰到西部人∶一个奇特的出言不逊的人,对别的乘客说∶ 俺是从密西西比黑树林里来的,俺在太阳晒著俺的时候,太阳有时也晒到一下┅┅俺是黑林子里的人,俺是┅┅俺那里没有皮肤光滑的人。俺们都是粗人。 这样的人凑合了一些新的字汇,其中尽是"开小差"、"吓得够呛"、"火冒三丈"之类的话;和"设备"、"想法"、"作法"之类空泛无边的词儿,几乎在任何场合都能使用。 边疆生活不用说是空虚寂寞的。孤独滋生了忧郁。尼科尔觉得"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幽默┅┅是一些经常严肃的人发出来的罕见的花朵,他们的见识清沏而不深奥,它主要依靠的是夸大和庄谐的揉合,这就产生了像黑人唱歌时用悲调唱滑稽歌词那种效果"。换句话说,西部的乐观主义,虽然只是那种说说笑笑幸福生活的产品,有时却是勉强的,几乎濒於绝望。失败,因为是可能的,也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东西。一个位於边疆的零落荒村,假如我们不设想它已经成了一个城市,如何能够存在下去呢?林肯的新塞勒姆就没有能够存在下去啊。 康斯坦斯·鲁尔克在她的《美国幽默》(American Humour, 1931)里说∶"边疆人民征服了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也征服了他们",把他们变成有一点差不多的野蛮人,也揭别人头皮,也为迷信害怕。这话说得不错,不过垦殖工作进展得快∶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每年平均移动十七哩。铁路轮船深入不毛之地。前不久还是边疆荒村,很快的就有了报馆(马克·吐温的汉尼巴尔镇有七家之多)、学校、教堂、律师事务所。爱默生以为是宗教把"钢琴这麽快的带到那些小屋"∶哈特对他说,不对,把钢琴带到那里去的是罪恶∶"是赌徒把音乐带到了加利福尼亚。是妓女把纽约的时装一股脑儿带到了那里。"毫无疑问,二者都发生过影响。美国妇女随时都想有所贡献,那是必然的,男人当然也不去阻止她们。狄更斯虽然不喜欢美国人的态度,也不得不承认在他整个旅程中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女人受到任何那怕是极其轻微的粗暴、失礼和怠慢的待遇"。如果说西部为它的粗野莽撞自鸣得意,它也急於要想温顺优雅。狄更斯碰到一个乔克托族酋长,说他极其欣赏《湖畔贵妇》和《马米扬》。肮脏污秽的矿城也都建起歌剧院,花钱听王尔德宣讲风雅。汤姆·索亚的那群强盗发现他们抢的是星期六举行的"主日学校野餐会",因为强盗的父母不许他们在安息日出去玩。 康斯坦斯·鲁尔克的说法,应该用托克维尔的话加以补充。他说,边疆居民,"一举一动都很粗鄙,不过他自己也是十八世纪劳动与经验的产物。"他的边疆移走了;森林开辟成平地了,猎物被人疯狂地滥捕滥杀。什麽事情都变了;在这意气风发急若狂飙的过程中,不时使人有极度悲哀之感。有一阵子,平底船和用马拉的驳船是内陆河上最好的运输工具。随後汽船代替了它们。旧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留下来的只有平底船船 之王迈克·芬克的传说和他的呼声∶"进步有什麽用处?那些欢乐、嬉戏、打斗都到哪里去了? 完了,什麽都完了!"沃德在他的《航程日记》里所表现的也是同样心情,"当时我还年轻(青春年少,不知有虚伪这个词),我在沃巴什运河上航行。"他在结语里说∶"那是唱《当年的好时光》这种歌的时代,汽船锅炉破裂了,把人抛到空中比纸鸢还高┅┅那些日子真快活┅┅"汽船的时代虽然比较长些,还是一种朝不保夕的工具。撒克里把它们叫做"纸板船",其中只有"一部引擎和值一万块钱的浮雕细工",这样的船不能持久,很容易撞上沙沙而突然完蛋。 西部的人对於环境的反应是极其自然的,假如对於那些人为的、转瞬即逝的东西不能致以正式的哀悼,就只有对它加以嘲笑。虽然边疆上没有神话,却很容易编造出来。这些传说中的英雄都是超人,可是他们也没有什麽惊人的地方∶他们是些可笑的人物,像迈克·芬克一类人物,吃得喝得比平常人多,也比别人能打斗,射得准。西南部英雄人物克罗克特,也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老肯塔克的一个旁支,据说老肯塔克能够吃一苹美洲豹,比水牛还能喝,一枪可以射穿月亮。"克罗克特传奇的发展最足以证明,心知其不实甚至伪造的边疆面貌都会有人相信。现实生活中的克罗克特是一个平庸的边疆居民,当过一阵子国会议员,後来对他那一党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甚感不满。民主党的敌对党自由党,急於争取边区选票,对克罗克特大加拢络,替他写了回忆录──把当时许多荒诞不经的故事统统写进他的回忆录里──把他捧上天去,说他是"半马半鳄",几十年来边疆居民都说他们是这样的动物。幸而他在德克萨斯争取独立的战争里在阿拉莫英勇战死,因而获得不朽。关於他的故事虽然是捏造的,但它适应一种需要,传说一定要有一个中心人物才行。如果克罗克特被人描绘成神,你也不能怪他。其他如水牛比尔和野比尔希科克,都是这个样子。尊贵的头衔──如法官、少校、上校甚至将军──都是编织神话时有用的饰物。有时这些衔头都是真的,有时真假参半,像基特·卡森在印第安人打劫过的篷车中找到一本描写印第安侦察员基特·卡森的廉价小说一样。 说真的,当时渗透在美国生活中的尽是些假货,它也是美国幽默中明显的成分,那是从贩卖木头肉?蔻的美国北部负贩,到哈特诗中写的袖里藏有二十四张杰克牌的中国异教徒那儿来的。当时美国的生活竞争性很强,欺诈的机会太多了。狄更斯说"精明"是受人欺骗之後得来的。特罗洛普也有同感,有人对他说,"你要明白,一个生活在边疆上的人非精明不可,否则他趁早回到东部去,说不定还得到欧洲去。在那些地方他可以生存。"人们把欺骗的丑恶编入笑话,甚至认为欺骗非常好玩。幽默减轻了欺骗的丑恶,就像月光把西部城镇横七竖八的街道美化了一样。假如人人都是主持演出的人,最终就不会有人上当了。你不可能老是欺骗所有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正忙著尔虞我诈。这是当时的理论,似乎还能行得通。巴纳姆骗人的玩意,使他越来越受人欢迎;只要他经常变换花样就行。乔奎因·米勒说他给印第安人用箭射伤了,比尔斯挖苦他有时用那条好腿一瘸一拐走路,那也只能证明在装假上还需要练习。要说米勒在做作上的确非常认真;他在晚年穿著一套克朗戴克人的服装跟著一个杂耍团到处跑,那是一套皮衣,缀著用金块制成的钮扣。说不定听众里面没人知道他一度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或者就是知道也没有关系,这也只是美国人前後不符逗人好笑而已。例如有些城镇根本就不存在,可是他们用画片宣传说它们存在已久,这情形怎不令人好笑呢?奥利芬特就曾在威斯康辛州访问过这样一个城镇∶ 在地政局看过这个城市的规划图以後┅┅,我们出去选择地皮┅┅;我们特别喜欢某几块地的适当位置,它们离开银行只有两个门口,位於一家大旅馆的转角处,面对码头,前面有一大片广场,後面通到汤普森街──事实上就在城里商业区最繁盛的地方,我们开始用钩镰在密茂的森林中开辟道路┅┅这片林子叫做第三街┅┅,直到我们到了一条小河的河床,我们沿河穿过纠结的短树丛(名叫西街),树丛尽头有一个沼泽,就是那主要的广场,沼泽那边长著几乎不能穿越的灌木丛,那正是我们地皮的所在地。 还有,谁能看到美国那些滑稽的地名而不发笑呢(除非是马修·阿诺德,美国人曾经得罪过的)? 比如说林肯,当他出发参加黑鹰战争(他在国会中嘲笑过这场战争)时曾经划独木舟一直由北京(Pekin)划到哈瓦那(Havana);两个地方都在伊利诺斯州境内。 西部幽默当然会反映这些滑稽可笑的东西。荒诞不经的故事。在殖民地时期即已风行美国(到一八二五年,曼昌森的故事在美国已经出过二十四版),一路向西延展,到达了虚伪的极度,例如说有一个猎人,受到熊和糜的夹攻,向岩石尖端开了一枪,子弹裂成两半,同时将两苹野兽杀死,岩石碎片还把近处树上的一个松鼠打了下来。猎人本来站在河边,枪的後坐力把他抛到河里,等他从水里爬了上来,发现浑身上下全都装满了鱼。 重要的是,这样的故事到处都在讲。这种事情需要一个讲故事的人和一批听众──要说也真巧,西部人就是喜欢听人讲话,不管讲话的人是叫卖商人、出风头的人、幽默家、牧师、国会议员,还是作家。爱德华.欣斯顿是英国的剧团经纪,不用说他对讲演这件事情也是很感兴趣的,他说∶ 美国全国是个极其庞大的讲演厅。讲坛从波士顿起,经过纽约、费城到华盛顿连成一条直线。阶梯看台的第一层是阿勒格尼斯山脉,楼座则设在落矶山顶。 有人夸张的说,英国军队早晨击鼓,声音不停地传开去,响彻全球,这句话也许有几分真实;不过更真实的是,在美国,讲演者的声音永不止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