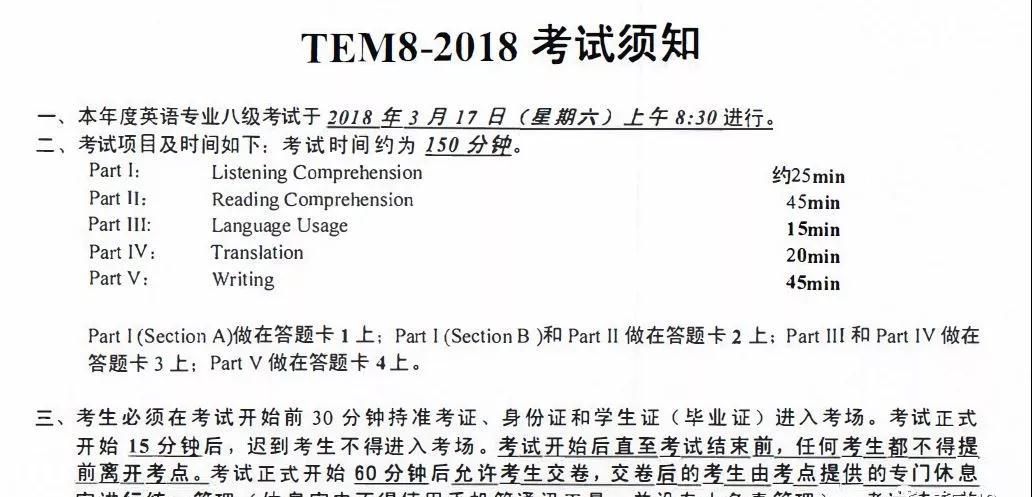美国宪法判例中的财产权保护
|
一、引言:姑且美国 在若干著述中,笔者曾不厌其烦地指出:与民法上的财产权不同,宪法上的财产权主要是私人针对公共权力的侵害而享有的财产权利,其中当然包括排除公共权力对私人之间业已确立的特定财产秩序进行不当干预的权利。[1]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国已经在一定意义和规模上存在了民法上的财产权保护规范,随着物权法规范的定立以及未来民法典的诞生,这种民法上的财产权保护规范体系将更趋完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没有分开宪法和民法上的财产权概念,就可能只满足于民法上的财产权保护,冲淡乃至“忽视了财产权之宪法保护这一课题本身的独立存在及其重大意义”,或者“把通过修宪完成这一课题的意义单纯地理解为是对民法上的财产权保护制度的一种确认或政治性的宣明,从而继续滞留于宪法乃是一部‘纲领性文件’的传统见地之上”。[2] 本文将可以有效地补助上述观点的奠立,但这不是其问题意识的核心。如所周知,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已经成为当今修宪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在此之际,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设问:中国要建立或完善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机制,是否可借鉴外国宪法中有关财产权保护的相关经验,以及可借鉴哪些国家的相关经验。显然,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赖于浩大、艰幸的研究活动,而本文则姑且以美国为对象,而且以其晚近的一个重要宪法判例为考察的焦点,引出这种研究的端绪。 像许多人耳熟能详的那样,美国联邦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财产权的保护条款,但其第5条修正案中规定:任何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非有正当的补偿,不得征用私有财产以供公共使用;另外,宪法第1条第10项中还规定;任何州不得制定损害合同义务的法律。前者被称之为征用条款(taking clause),其含义通过第14条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而适用于各州;[3]而后者则是通常所谓的宪法上的“合同条款”。美国宪法正是通过这些条款来间接保护宪法上的财产权的,[4]其中,征用条款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如果说根据第5条或第14条修正案的规定政府对私人财产可拥有征用权,那么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修正案中的有关规定乃是一种人权条款,原则上不能推断出公共权力的某项权限。在美国,一般认为政府的财产征用权(eminent domain)乃是属于主权中所固有的一项权限,而征用条款并非赋予这一权限,只不过是规定了其行使的条件而已。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征用必须补偿。可以说,美国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其制度的核心不在于禁止政府对私人财产权的规制,而在于设定征用补偿这一条件性的阻却机制,至于在什么情形下加以补偿,如何补偿,则需要在某种有效的宪法制度下所进行的具体解释,那种有效的宪法制度就是宪法诉讼,而其所产生的宪法判例就是那种具体解释的权威文本。离开了宪法诉讼制度和宪法判例制度,美国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中有关的征用条款同样会成为一种“悬之高阁”的条款,犹如我国宪法中的大部分条款,甚至犹如我们在不久后的修宪中将可能引入的那种私人财产权保护条款。 但美国毕竟不同,其征用条款成功地在上述两个动态的制度下进入了运作。在传统的实践中,美国首先严格区分了“征用权”与州的“警察权”(police power)这两个概念,对政府行使征用权而对私人财产所实行的规制予以补偿,而运用警察权的规制(包括剥夺)一般则不需要补偿。但这便产生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即:何种财产规制属于警察权的规制,而何种财产规制则属于宪法上的征用(taking)。这一问题自然反映在日常的有关宪法诉讼之中,成为宪法争议的一种重要焦点,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宪法判例。 二、路卡思案的梗概 首先我们来看路卡思诉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委员会案(Lucas v. 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5]这是一个典型的、也是较新的判例,由此我们回溯过去的判例,就可纵观美国宪法上财产权保护的基本概况。 路卡思案的发生肇始于美国的海岸环境保护。1972年,联邦议会制定了《沿岸区域管理法》,[6]规定各州可制定海岸环境保护的计划,并通过根据该类计划拨给一定财政补助等方式,诱导各州加强海岸环保,从而间接地达到保护海岸线的目的。该法施行后,各州果真先后立法保护海岸环境,其间,南卡罗来纳州也于1977年制定了一部《沿岸区域管理法》。根据该法的规定,海滨以及临接海滨的沙滩地域均为指定的critical area (以下译为“保护区”),在区内建造住宅性质的建筑物受到禁止,对土地的利用也受到相应的限制。但因为这种指定保护区的范围相应较窄,不足以充分防止海岸线的侵蚀现象,该州遂于1986年设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并根据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于1988年制定了《沿海区域管理法》。[7]新法扩大了指定保护区,并与1977年的《沿岸区域管理法》一样,对区内的土地利用实行规制。 本案当事人路卡思(Lucas)在Palm岛上从事不动产开发,建造了一个命名为“野丘”(Wild Dune)的住宅群。1978年路卡思自己也入住此处,并于1986年以私人资金97万5000美元买下了另外两块住宅用地。这两块地皮距离海滨约90米,根据1977年的《沿岸区管理法》不属于指定保护区,但根据1988年的《沿海区域管理法》则属于该类区域,被禁止建造居宅性质的建筑物。于是,路卡思便以该法的土地利用限制乃相当于不予补偿的财产征用(taking)为由,向州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委员会[8]作出损失补偿。 在一审法院上,路卡思一方对于本案中的州法乃属于州的警察权(police power)的正当行使这一问题不予争辩,仅要求损失补偿。法官认可了路卡思的要求,判决州一方对他作出120万美元的损失补偿,理由是:路卡思1986年买下案中的地皮时,该地被认定为住宅用地,可供建造住宅之用,而随着1988年新法的成立,该地则因其土地利用规制而失去了合理的经济利用(reasonable economic use)的可能性,完全成为“无价值”(valueless)的东西。 然而,在上诉审的州最高法院中,法官以路卡思对州法的有效性没有争议为理由,认定该法乃是为了防止公共危害(public harm)的发生,在宪法的征用条款上无需作出损失补偿。州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乃是于1991年作出的,其实早在其口头辩论程序结束后的1990年6月,南卡罗来纳州的那部《沿海区域管理法》又已被修改,修改后的法律规定设立一种特别许可(special permit)制度,州委员会可根据个别的特殊情况对特定的住宅用地的利用予以许可。 但路卡思还是将本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三、先例及其问题 显然,本案颇为复杂,但其主要涉及的是:政府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私人财产的规制是否构成“征用”,从而被规制的私人财产是否可获得宪法上的财产权保护。 在美国宪法上,征用的形式本来颇为宽泛。除了对土地所有权的剥夺可视为征用之外,对财产权的其它形式的规制,包括妨害财产的使用,均有可能被认定为征用。此外,即使是无形财产受到剥夺,也可能构成征用,为此需要对其加以补偿。但如上所述,由于要区分征用权与警察权,所以确认某种财产规制是否属于征用,就不得不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法律问题。 有关这一点,联邦最高法院早已确立了权威判例。1922年的马洪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在此案中,原来的一方当事人从一家煤矿公司那里买进一块土地的地面权,当时双方之间成立的让渡条件之一是该煤矿公司可继续保留在其地下开采煤矿的权利,但此后州法规定禁止有可能对地面居住建筑物导致危险的地下采矿,该当事人遂据此向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禁止煤矿公司继续在那块土地下采煤,而煤矿公司自然作出对抗,从而引发了一宗宪法诉讼。案件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该法院的判决认为:案中的州法对财产的规制,不能属于警察权的运用,因为欠缺可使之正当化的公共利益。质言之,象此案这样对财产权的规制已达到了一定限度的情形下,应认定该种规制属于征用,即必须作出补偿。[9] 1928年联邦最高法院又在Miller v. Schoene一案中遇到了必须判断一项财产规制是否构成征用的问题。[10]在此案中,弗吉尼亚州于1924年颁布了一部有关控制香柏树病的法律,因为这种病毒对邻近的苹果树等植物会造成有害传染,而苹果种植则是当时该州的一项主要农副产业。根据这部州法,案中的原告被命令砍伐其所拥有的大片红香柏树,以免其病毒传染附近的苹果树,便诉至巡回法院,巡回法院认可了上述命令的合理性,但裁定须支付原告砍伐与搬迁树木的费用100美元,至于原告因丧失大片红香柏树以及由此所招致的地皮跌价等损失,则得不到补偿。此案最终也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维护了上述判决,理由是在此案中,砍伐香柏树而保护苹果树乃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属于警察权的正当行使。[11] 从上述两案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征用认定是颇为复杂的,而这在土地利用规制上更成为难题。在1926年欧几里德一案的判决中,[12]联邦最高法院判示:新型的城市规划法要求将工商业设施从市民的居住区中排除出去的措施,乃相当于依据警察权的规制,因此导致的财产贬值的损失可不予补偿。然而,对于在何种情形下财产规制乃是超出了警察权的正当行使而构成需要补偿的征用这一问题,此后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在前述的马洪案中,霍姆斯大法官曾提出一个简明的标准,即:“但凡财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对其进行限制,但限制一旦过多,则可视用征用”,为此法院实际上判示:某一规制对财产价值所造成的损害一旦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就可构成“征用”;但在1962年的Goldblatt v. Hempstead一案的判决中,[13]最高法院却认为决定某一规制是否构成征用并不存在固定的公式,为此采用了对规制的目的、手段以及损害状况加以具体检讨的方法,判定案中导致当事人所拥有的财产完全失去价值的规制乃属于警察权的合理行使。该种个案分析的方法此后长期得到广泛的维持,并沿用于诸多土地规制以外的个案之中。[14]这种判例自然引起了理论界上的各种争论与分歧,甚至导致联邦下级法院和各州法院有关判例的混乱,使因为规制而受到影响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处于不安定和不确定的状况之中。[15] 在这种情形之下,联邦最高法院就不得不有待于在一个适当的案例中为征用补偿确立一个确定性的规则。前述的路卡思案,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案例。 四、新的判例1992年,联邦最高法院对路卡思案作出了宣判,9位全体大法官以6 : 2形成多数意见,作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判决。 该判决的法庭意见由斯格利亚大法官(J. Scalia)执笔。对此,伦奎斯特大法官(J. Rehnquist)、奥康娜大法官(J. O‘Cohnor)等人持赞同意见,肯尼迪大法官(J. Kennedy)另有补充意见。 法庭意见主要有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就1990年州法修改为止这一段期间的征用来说,本案具备了提出宪法诉讼的成熟性(ripeness)。 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法律技术性的问题,判词的要旨是这样的: 正如被上诉人州委员会亦指出的那样,本院迄今为止均判示:当某一种土地规制引起争议时,作为判断其合宪性的前提,特定的土地可允许如何利用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得到明确。[16]州委员会依据这些判决作出主张:对于上诉人路卡思来说,由于1990年州法已得到修改,修改后的州法也已开辟了特别许可的途径,为此在原阶段的意义上,本案欠缺由本院受理其上诉所需要的争诉之成熟性。然而州最高法院未曾认为有必要完成这种程序,而直接审理了本案,并判决系案的州法合宪。 诚然,州最高法院的该判决并没有导致路卡思不能在1990年州法修改后作出可以作出的救济请求,但这一判决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即:在上述州法修改之内的期间内,路卡思被剥夺了建造住宅的权利,并不能得到损失补偿。本院在1987年格伦代尔市英国第一福音路德会诉洛杉矶县一案[17]的先例中已经确定:根据宪法的征用条款,对于一时性的征用也必须作出损失补偿。而在本案中,从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所涵盖的范围来看,路卡思显然被封闭了就过去的损失而取得补偿的途径。为此,就本案而言,在成熟性的要件上,本院所被允许的裁量判断范围之内的“慎重的成熟”(prudential ripeness)就可成为一个问题,而要求穷尽行政救济的程序则不能说是一种审慎(prudent)的裁定。 (二)对具有经济利益的任何利用权的剥夺均构成“征用”。 这是本案法理论述的关键部分,对此,判词的论述主要可概括如下: 直至1922年的马洪案为止,征用条款所适用的对象一直被限定于财产被直接充作公用、在实质上等于财产的占有受到剥夺的个案。然而正如这一判决所显示的那样,霍姆斯大法官已经认识到:对于物理性的公益征用,为使财产权的保护在具有意义的形式下进行,作为其当然的前提,政府对包含在财产的所有权中的各种利益的重新定义的权限,有必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这诚如霍姆斯大法官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所言:“但凡财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对其进行限制,但限制一旦过多,则可视用征用”。 然而,上述的判决[18]对于什么情形乃属于限制的“过多”这一问题,基本上没有给出指引。在此后的70年间,我们一直面临着就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序化的基准上作出判示,以便立足于具体事实而解决各种案件。 不过,无须对通过限制财产权而力图实现的公共利益的内容进行个别的审查,但凡必须补偿的情形存在两个范畴。一个是对财产所进行的物理性侵害;另一个则是对经济上的有益利用(economically beneficial use)的完全损害。本案的情形即属于后者,其在经济上的有益利用近乎不可能的状态,乃相当于财产被征用的情形。以保护土地的自然状态为目的规制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典型。这种对自然的保护,也存在支付损失补偿、即在公益征用的程序下进行的事例。而在防止严重公害的名义下,以规制的形式所进行的这种限制,将本来应由全社会来承受的负担强加给一部分私人的危险颇大。 (三)所谓禁止“有害性利用”的正当化不应予以认可。 有关这一点,判词指出: 州最高法院判定本案中的规制行为合宪,理由是系案州法上的限制对于保护州民的生命、财产乃是必要的,其所禁止的开发行为属于对上述公共利益的一种有害性的财产利用。诚然,本院曾在一系列判决中,以有害于公共利益为理由,将没有支付损失补偿的财产权之限制加以正当化。[19] 然而这只是对在征用条款存在的前提下,警察权的行使为何无须支付损失补偿这一点进行说明时所做的尝试而已。晚近的各个判例表明,当今警察权的行使目的并不限定于排除公共的危害,实现公共福利的增进均被视为州行使警察权的正当目的。 某一规制到底是属于防止公共危害还是属于增进公共利益,必定因人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而见仁见智。为此,像原审法院那样单纯地把立法机关的所谓“为防止公共的危害”这一判断加以囫囵吞枣,并判定无须补偿,乃等于将马洪案判决中所判示的这一法理化为乌有,即:警察权的行使在宪法上具有界限。 导致经济上的有益利用失去一切可能性的规制可例外地符合宪法,仅限于这样一种情形,即:被禁止利用的利益,从原初开始就不包含在财产权人的权原(title)之中。一般而言,人们预期(expect)到自己的财产因州的立法而受到影响。然而,与受影响较多的非不动产不同,就土地来说,州委员会一方认为其已经附带了一种默示性的限制,即可能出现经济上有价值的利用完全受到否定的情形,这一理解与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的征用条款中所记凝结的“历史性合意”(historical compact)相龃龉。为此,那种规制可不必做出补偿的情形,仅仅限于把并非立法机关所新订立的、业已包含在普通法上的财产权中的制约,即在各个州的物权法(包括公物法在内的广义的物权法)以及排除妨害财产权益法(State‘s Law of Property and Nuisance)上原已内在蕴含于财产权之内的制约加以具体化的那种场合。 路卡思在其土地上建造住宅的行为,很难可理解属于这种例外的场合,但这是州法上的问题,应由接受发回重审的州法院加以判断。 肯尼迪大法官的补充意见是:法庭意见并非判示存在一时性的征用。必须考虑上诉人是否具备开发的意思和能力以及是否因州的规制而受到阻碍等因素。把例外限定于排除妨害财产权益法的场合有过于狭窄之虞,应以保护“合理的、有投资背景的期待”(reasonable, investment-backed expectations)为基准。 五、确定性规则的争议性 应该承认这一判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要选取本案,不仅乃由于它的判决引述了美国宪法上有关财产征用问题的许多重要判例,所以作为一个判例,其内容十分饱满,便于较为全面地了解美国有关判例的演变或展开,同时还由于这份判决正是针对上述的问题状况,试图就征用补偿这一方面提出了一个确定性的规则。由于判词的上述论述颇为复杂,我们在此可把这一规则的主要内容简单地概述如下: (1)某一规制如果导致财产的经济上的有效利用几乎失去可能的话,那么原则上应视为征用,必须做出补偿; (2)但这种规制在例外的情形下也可无须补偿; (3)不过,这种例外又仅限于根据各州的物权法或排除妨害财产权益法也须或也可作出同样规制的场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则中的原则部分与例外部分均可能存在争议性。其实,本案判决时,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中就存在激烈的意见分歧,布莱克蒙大法官(J. Blackmun)与史蒂文斯大法官(J. Stevens)分别写了反对意见,反对意见所针对的就是上述这一点。其中,布莱克蒙大法官反对意见中的第2点以及史蒂文斯大法官反对意见中的第3点,即是殊为有力的批评,值得有兴趣者细致玩味。 布莱克蒙大法官在反对意见中居然写道:“今日,本院为了杀死一只老鼠而发射了导弹”。他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不能审查本案一审的认定,但对基于系案中的规制而使案中的土地完全失去价值的这一认定,则存有极大的疑义。提取本案而作出这样的重要决断,极为不妥。这是他反对意见中的第1点,主要内容如下: 在过去40年间中约一半的期间内,路卡思的土地一直处于岸边或一直受到潮汐的侵蚀。本案中的州法乃是为了在保护人的生命或财产免受风暴或高浪的灾害、保护必要的海岸区域所制定的。路卡思对此也完全没有异议。正因如此,原审法院认可了州立法机关的意旨。 本案还欠缺由本院受理上诉所必需的纠纷的成熟性这一要件。法庭意见认为就其中一时性的征用这一点来说该要件可得到满足,但路卡思既没有向州委员会申请建筑许可,也没有对保护区指定的划线位置的合适性提出争议。即使在宪法上行使上诉审查权没有问题,但行使这一权限还是不够明智的。这是因为,一审法院对本案土地所作出的完全失去利用价值的这一认定可能违背了事实。实际上,即使在本案中所涉及的规制之下,上诉人也没有失去土地所有权的本质要素,包括排除他人侵占的权利,并仍然留下用于野营或停放移动车辆等用途。一审法院乃是将“价值的减少”(less value)与“无价值”(valueless)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布莱克蒙大法官反对意见的第2点是认为法庭意见违背了先前判例。理由如下: 它无视了迄今为止联邦最高法院的“无数先例”,即:立法机关的判断应当受到尊重。同时,它还无视了迄今为止的一个先例而建构了笼统的规则。这一先例就是:在判断财产权规制在何种情形下才属于“征用”这一问题时,重视诸个案的事实,并综合考量各种要素。本判决就有关使财产完全失去价值的规制所确立的、所谓该种规制一旦没有依据普通法中的排除妨害财产权益法、物权法的诸准则便属于征用的这一规则,在以下几点上值得异议。 在法庭意见所列举的Mugler判决等一系列先例中,虽然当事人均主张财产因受规制而完全失去价值,但法院并没有将这一点作为决定性的要素,而是鉴于实行该规制所追求的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判定对其规制的合宪性。本判决所认可的例外,正是一种这样的明证,即:无法完全否认规制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在内容上的必要性。 法庭意见以非客观性、相对性为理由否定了“有害性利用”的准则,并为排除价值判断而从普通法中寻求自由的客观性基准,然而这种规则具有两个缺陷。第一,在对什么东西之中多少东西被剥夺、即被剥夺的东西的比例进行判断时,如何求得其分母(denominator)是无法一概而论的。例如,在1987年的Keystone Bituminous Coal Association v. DeBenedictus一案[20]中,法院对禁止招致地面塌陷的煤矿开采的立法作出合宪判决。在此案中,地面的土地所有权人转让给煤矿公司的地面支持权(support estate)被确认为仅属于财产的一部分,但判决中的少数意见则认为其乃属于独立的财产,并完全受到损坏;第二,法院在对何者为私人之间的财产妨害行为、何者为公权力的财产妨害行为作出判断时,向来对各种竞合的利益加以比较衡量,从而作出综合判断。而撇开价值判断,并从排除妨害财产权益法中寻求自由的客观性基准,则是不可能的。此外,法庭意见中就有关征用条款的历史理解也是错误的。 而史蒂文斯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则包括以下6点: (1)就本案而行使上诉管辖权乃是不明智之举。 (2)法庭意见不仅有悖于本法院一向否定确立笼统性规则的先例,而且还有悖于即使在财产因规制而完全失去价值的情形下亦认同未必均属于“征用”的这一先例。 (3)土地失去100%价值就予以全面补偿,但如果仅失去95%的价值则完全不予补偿,这种规则具有过大的任意性。同时,对“财产”既可进行广义的界定,也可进行狭义的界定,正如法院在处理Mugler案时所显示的那样,[21]任意性的操作还是有可能的。 (4)诚然,宪法上征用条款的存在目的,乃是为了防止政治过程中的多数派将本来应由全社会承担的负担强加给(singling out)少数人。然而,财产价值减少的大小与上述这一危险之间不一定就具有关连性。 (5)迄今为止,我们均认同:为了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不断变化,立法机关可填补普通法(Common Law)的缺陷,并对向来合法的东西加以禁止或限制。然而,如果根据本判决法庭意见所持有的、从过去的法中寻求可以限制的基准这一逻辑,即使在禁止向来合法的石棉、香烟制造的情形下,也变成需要作出补偿。在经济、环境的变化速度和重要性与日俱增的当今,规则有必要面向未来,而非面向过去。 (6)根据在本案中成为问题焦点的规制,受到限制的土地在范围上颇为广泛,这种限制不仅止于像本案中这样的未用地,而且还扩及既用地。从本案中成为限制对象的土地的特殊性、受限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本案中的立法所具有的目的的重要性来看,即使土地因此而完全失去价值,也不相当于征用。 除了上述布莱克蒙大法官与史蒂文斯大法官的反对意见,苏特大法(J. Souter)则发表了受理本案的上诉并不适当的声明,理由是一审的事实认定存有疑义,不应接受本案的上诉。 六、结语 路卡思一案最终基本上以路卡思的胜诉而告终。这个结局似乎也可说明了在现代的美国,对财产权的保护其实又进一步趋于强化。这在联邦最高法院就征用补偿所提出的那个确定性的规则中也可以看出端倪。在这一规则中,作为制约财产权之正当依据的公共利益观念退居其后,而规则的形式性则较为突出。而且在美国,这种形式性本来就具有颇远的渊源,人们至少可以从霍姆斯大法官在马洪案中所提出的那个简明的标准中领略到这一点。 通过本文的评介,我们还不难看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其实不是一种简单的法的实践。首先,它本身就涉及非常复杂的宪法运作问题,离不开宪法上所设立的财产权保护条款之外的其他具体制度的有效配合。就此反观当下的我国,我们不要天真地期望通过在宪法文本中插入一套宪法条文就可以建立起有效的财产权宪法保护机制,也不要误认为在修宪中引入私人财产权保护条文就会导致所有制的变更,相反,财产权宪法保护的实际命运如何,具体内容怎样,靠凭一套宪法条文不行,而端视对这种条文的解释和运作。美国如此,迄今仍没有建立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制度的中国更不可能例外。 其次,我们还可看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还涉及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就本文所着重介绍的路卡思案来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间意见的分歧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本来,在宪法判决中,大法官们意见分歧的存在并不足为怪,在西方许多国家的违宪审查实践中,宪法判断主体内部均经常存有各种不一致的意见。尽管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上述路卡思一案判决中的意见分歧,则可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警省意味。即使我们有朝一日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甚至引入了判例制度的某些合理的机制,以便有效的保障宪法上的权利,还是要看到,像财产权这样的宪法上权利的保障,仍然需要面临艰深的理论和琐细的技术问题。也许当下不少的中国学者均希望从美国宪法的财产权保护规范及其运作实践中吸取一些对确立中国宪法上的财产权保护制度有所助益的要素,但路卡思一案的判决显示:虽然人们笼统地以为判例制度更便于厘定抽象的宪法概念,但即使在这个较新的权威判例中,美国法院也没有彻底提供一个没有争议性的法理结论。有鉴于此,倘若我国真的能够在宪法上确立财产权的保护机制,那么,综合和总结各国宪法的有关规范、理论和实践中的经验,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宪法理念的财产权保障的理论和技术,就成为下一个至难的课题。 1] 笔者对有关财产权宪法保障问题之研究的著述,始有《论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载《法学》1999年第3期;其详篇《财产权宪法保障的比较研究》,载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2卷所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以下;继有修订性的论述可见拙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以下;近有《针对国家享有的财产权:从比较法角度的一个考察》,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孙笑侠、林来梵、夏立安(编):《返回法的形而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以下所收。 [2] 前引拙文《针对国家享有的财产权:从比较法角度的一个考察》,孙笑侠等编,前引书,第153页。 [3] 该条修正案中规定,任何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众所周知,根据美国宪法上有关人权条款的并入理论,第5条修正案的内容可被该条所吸收。 [4] 有关通过合同条款而对财产权进行间接保护的问题,可参见林来梵、胡锦光:《西岸宾馆诉帕里什案》,载《判解研究》2001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以下。 [5] 505 U.S. 1003 (1992) [6]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 [7] Beachfront Management Act. [8] 即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乃属于州的一个行政委员会,以下简称“州委员会”。 [9] 即宾夕法尼亚煤碳公司诉马洪一案(Pennsylvania Coal Co v. Mahon), see 260 U.S. 393, 43 S. Ct. 158, 67 L. Ed. 322 (1922).有关该案,另可参见李进之、王久华、李克宁、蒋丹宁:《美国财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以下的介绍。 [10] 有关此案,亦可参见另可参见李进之、王久华、李克宁、蒋丹宁,同上书,第191页以下。 [11] See 276 U.S. 272 (1928) [12] Euclid v. Ambler Realty Co., 272 U. S. 365 (1926). [13] See 369 U. S. 590 (1962). [14] 如著名的Ruckelshaus v. Monsanto Co.一案,see 467 U. S. 986 (1984);又如Connolly v. 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 see 475 U. S. 211 (1986).在这些案件中,法院具体考量了以下三个要素,即:(1)政府规制行为的性质,(2)经济上的影响,(3)对合理的、具有投资背景的期待的损害。 [15] See Berger & Kanner, Thoughts on the White River Junction Manifesto: A Reply to the Gang of Five‘s Views on Just Compensation for regulatory Taking of Property, 19 Loy. L. A. L. REV. 685 (1986). [16] 判决引述MacDonald, Sommers & Frates v. Yolo County以及Williamson County Regional Planning Comm’n v. Hamitton Bank的判例,前者见477 U.S. 340 (1986),后者见473 U.S. 172 (1985)。 [17] First Engl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Glendale v. County of Los Angeles, 482 U.S. 304 (1987). [18] 这里指的是上述马洪案的判决。 [19] 判决引述涉及禁止造酒的Mugler v. Kansas案[See 123 U.S. 623 (1887)]、涉及禁止在后发性市街化地域上制造炼瓦的Hadacheck v. Sebastian案[See 239 U.S. 394 (1915)]、涉及禁止在后发性市街化地域内从事切石业的Goldblatt v. Hempstead [See 369 U.S. 590 (1962)]以及上述的香柏树案(Miller v. Schoene案等判决。 [20] See 480 U.S. 470. [21] 其中引Mugler一案的事例,指出在该案中,酿酒厂完全失去了价值,但法庭意见却把整体的土地、建筑物视为“财产”,从而认为并非完全失去价值。 |